博鱼体育官网 boyutiyuguanwang 分类>>
一场跨越四博鱼体育- 博鱼体育官网- APP下载世界杯指定平台十年的逆转
博鱼,博鱼体育,博鱼官方网站,博鱼体育登录入口,博鱼官网,博鱼体育登录入口,博鱼体育官网,博鱼体育下载,博鱼app下载,博鱼注册网址,博鱼体育官方网站,博鱼app,博鱼体育入口

1978年11月,德国,沃尔夫斯堡。在大众汽车工厂门口,一名警卫面对着几位身穿中山装、面孔陌生的东方来客。为首的一位老人,头发花白,神情严肃,开口对他说道:“我是中国的机械工业部部长,想与大众公司的负责人对话。”
这位部长叫周子健。面对这位从火车站徒步而来的中国客人,警卫惊得下巴差点掉下来,他赶紧设法联系上了当天恰好在公司的大众董事施密特。同样惊讶的施密特,立刻让保安放行。
改革开放之初,由于与世界隔绝太久,即便是周子健这样的高级官员,这也是第一次出国。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亲眼看看世界现代汽车工业的面貌。而在他们身后,是几代汽车人未竟的梦想和近三十年近乎停滞的沉重现实。
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的帮助下,长春郊外的荒原上曾建起宏伟的第一汽车制造厂,但经历了50年代的初创后,中国的汽车工业便陷入了长期的停滞。当世界汽车工业在六七十年代大步跨越时,中国的道路上行驶的,依然是解放、东风、红旗、上海、北京吉普这几种修修补补了三十年的仿制车。
生产方式更是原始得令人心酸。在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上海汽车厂,工人们只能用榔头、铁锤一下下敲出轿车的外壳和零件。一个大的覆盖件,要经过几万次的敲打。当时还没走进车间,就能听到此起彼伏的“打击乐”。来自欧美和日本的汽车公司代表参观后,留下的评价一致且刺耳:中国的汽车工业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
榔头敲不出好车。国产车的质量问题百出,当时民间有编的顺口溜:“远看摇头摆尾,近看呲牙咧嘴,停下来漏油漏水。” 就连接待外宾的红旗轿车,去机场都得多备几辆以防半路抛锚。时任副总理的万里,就曾被自己的红旗车丢在出差路上,最后坐公交车才回的家。
正是背负着这样的历史,周子健一行人走进了大众的工厂。眼前的一切,都像是一场来自另一个文明的展示:先进的自动化设备,训练有素的工人,一辆辆崭新的汽车安静而高效地从流水线上完成装配。这一切,都让他们想起上海车间里那经年不息的“榔头打击乐”。大众一间工厂每天下线辆——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中国一年的轿车总产量。
总设计师那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还没问世,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见识到了先进科技带来的惊人生产力。
代表团当时所见的,是大众汽车在经历“后甲壳虫时代”危机后,凭借技术革新实现的强势复兴。70年代中期,大众曾因其标志性产品甲壳虫平台老化而陷入生存危机,但转机出现在1974年,当时面对第一次“石油危机”,大众推出了高尔夫第一代车型。这款车一举奠定了大众此后数十年的行业地位,全球销量近700万辆,帮助大众在1985年首次登顶欧洲汽车制造商的宝座。
大众的成功,背后是一套严谨到近乎残酷的质量体系。为了验证车身强度,试验台用“液压脉冲”对车辆进行高强度扭转;为了测试耐久性,整车被置于气候室中,经受长达数月的酷暑与极寒考验。测试完成后,车辆会被完全拆解,由专家对每一个零部件进行最终分析。
正是在这种巨大差距的直观感受下,随团的上海代表蒋涛在座谈会上,向周子健部长提议,直接询问德方是否有意与上海合资经营轿车厂。这个即席提议,得到了大众董事施密特先生热烈得超乎想象的回应,他将双手高高举向空中,大声说:“我双手赞成!” 他表示,大众愿意出资金、出技术,将最新的车型提供给上海选择。
德国人的热情不难理解。70年代的石油危机,让高油耗的美国车节节败退,省油的日本车异军突起,大众同样面临巨大压力,急需寻找新的市场。而百废待兴的中国,无疑是地球上最具潜力的那片蓝海。更巧合的是,就在不久之前,傲慢的美国通用汽车刚刚拒绝了中国的合作提议——他们不会想到,自己失去的是史上最大的商机。
站在今天回望,不得不佩服德国人的眼光。80年代的中国,仍是“自行车王国”,拥有一辆轿车对普通人而言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毕生的梦想不过是拥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
中国薄弱的工业底子给合资经营带来了很大困难,无论技术、管理,还是相关的法律、制度,国内都有许多空白亟待填补。桑塔纳生产线的电子设备运抵上海时,在厂房的另一半,中国的钣金师傅们还在用榔头敲着自己的上海牌轿车,这种魔幻的场景便是当时中国工业与西方发达国家巨大差距的一个缩影。
直到三十多年后,在每年的上汽集团校园招聘会上,HR都会讲到这个例子:按照大众的质量标准,当时的中国能制造什么?答案是,只能提供汽车收音机上用的天线。合资项目进行了两年,一辆“上海制造”的桑塔纳,国产化率仅有2.7%。扒开来看,只有轮胎、收音机、天线和标牌四样东西是中国制造的。
一个方向盘,更是将这道鸿沟展现得淋漓尽致。过去,中国工厂对方向盘的测试指标只有6个,而桑塔纳的标准清单上,密密麻麻地写着106个。这背后,是两套截然不同的工业哲学。中国的体系,关心的是基本功能实现;而德国的体系,是建立在系统化流程、穷尽式验证和深度协同之上的,旨在从源头预防一切可能的失效。
首任德方经理马丁·波斯特在他的回忆录《在中国的1000天》里,为这段历史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观察。他形容这个项目是从“零以下”开始的。他发现工厂的油漆里含有剧毒的汞,当他提出警告后,这些油漆并没有被妥善处理,而是被倾倒进了附近的河里;整个工作环境弥漫着“计划经济心态”,浪费现象严重,员工缺乏工作积极性和个人责任感。
当有官员责问国产化为何进展缓慢时,上海厂的老师傅无奈地回答:“我们是用50年代的设备,生产80年代的轿车。”这句回答,道尽了那个时代的辛酸。
最终,桑塔纳项目超越了一个商业合资的范畴,它变成了一个由市场驱动的、痛苦而昂贵的全国性工业培训平台。为了拿到订单,全国数百家零部件厂商被迫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去理解并满足那106项测试指标背后的逻辑。正是这个过程,在实践中锻造了中国现代汽车零部件工业的最初基石,也为一个更宏大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马丁·波斯特在回忆录中还有一句话描述他对当时中国的印象:“在那里,是生活在欧洲的人几乎无法想象的贫困境地。可同时,我又能感受到整个国家对改善的期盼。”
1994年,德国大众汽车与工会签订了一份保障员工利益的重要协议:35年内,也就是直到2029年之前,大众在德国境内不得随意裁员,为员工提供足够的工作安全感。对当时的德国人来说,进入大众就意味着拥有了一份待遇不菲的铁饭碗。
大众敢于签这份就业保障协议的底气在于,当时大众汽车处于稳定增长期,凭借高尔夫等车型吸引了大批消费者,全球销量超过350万辆,仅次于丰田和通用。而在刚要起飞的中国市场,大众的布局更是领先对手一步,即将迎来躺着赚钱的黄金时代。这种前景,保障了德国工人阶层不用996也能衣食无忧岁月静好。
那是一个合资车瓜分中国的时代,而大众成为最大受益者。北京街头的自行车洪流,逐渐被滚滚车流所取代。对于提前布局、手握桑塔纳和捷达两张王牌的大众汽车而言,这无异于天降甘霖。凭借先发优势和“德国品质”的光环,大众在中国市场几乎是断层式领先。
这场盛宴的丰盛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中国不仅是大众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更是其利润的核心支柱。2014年上半年,大众集团全球营业利润为62亿欧元,而其在中国的两家合资企业就贡献了高达26亿欧元的利润,占比达到惊人的42%。这意味着,大众在世界其他所有地方辛苦忙碌的总和,还不如在中国赚得多。
德国豪华品牌BBA(奔驰、宝马、奥迪)同样在中国市场赚得盆满钵满。一汽生产的奥迪A6,凭借其稳重方正的造型,毫无悬念地成为了各级政府部门的标配,“官车”的形象深入人心,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就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2016 年,大众第一次超越丰田成为全球销量第一的车企,之后几年也基本维持了1000万辆以上的销售规模,而且这还是在2015年“排放门”的阴影下完成的。“排放门”事件中,大众因尾气排放造假被美国环保局罚了300多亿美元,但在中国市场却毫无影响,堪称大众最牢固的核心基本盘。
中国汽车工业早期对外开放的核心战略——“以市场换技术”,在现实中却步步为艰。市场确实让出去了,但核心技术似乎并未如期而至。
前机械工业部部长何光远曾将这种合资模式比作“”,尖锐地批评中方国有企业满足于对外国车型进行最小化的改动和组装,从而产生了路径依赖,丧失了从零开始自主研发整车、掌握核心技术和专利的动力。
面对飞速增长的国内市场,合资公司最轻松的策略就是加快引进。海关人员甚至发现,有些以零部件名义进口的集装箱,打开检查却发现是只差轮胎还没安装的汽车,所谓合资国产,只是安个轮胎而已。
在这种模式下,外资品牌在中国市场享受着饕餮盛宴,而中国消费者接受着含有巨额技术转让费和品牌使用费的车价。对比隔壁的韩国,现代汽车同样从引进西方技术开始,只花了不到十年时间,就开始走向世界。
90年代,已有上亿身家的李书福对外宣称要投资5亿造车,却备受白眼。当时的产业政策门槛极高,最低投资需15亿,且强调以三大国企为主。李书福到机械部请求批准,连门都进不去;去上海采购配件,供应商的工程师听闻他5亿造车的计划,扭头就走。
面对重重困难和旁人劝阻,他抛出了那句名言:“造汽车有什么难的,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两张沙发吗?” 你可以说无知者无畏,但在那个草创探路的蛮荒年代,正是这种无畏成了第一代造车人摸索前行的动力。
另一边,在一汽担任总装车间主任的安徽人尹同耀,跑到芜湖一家村办工厂,开始了一个叫奇瑞的自主汽车品牌梦想。由于有国有身份,他们的造车之旅要顺利得多。尽管如此,奇瑞还是向上汽出让了20%股份,才换得造车资质,用尹同耀的话说:“即便做出如此大的让步,也还是托前华东野战军老领导的帮助,才有了和上汽合作的机会。”
站在当时,很难想象这样一群草台班子般的造车人,有机会在将来与世界巨头掰掰手腕。
2015年9月,美国环境保护署发布了一份针对大众汽车集团的违规通知,如同一枚投入平静湖面的炸弹,引爆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风暴。这不仅仅是一家公司的丑闻,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黄昏,一个以“德国制造”为信仰的工业神话,开始崩塌。
丑闻的核心,是一种被称为“失效保护器”的软件。这个精心设计的程序能够识别车辆是否处于实验室测试环境中,并完全启动尾气排放控制系统以符合法规标准。然而,一旦车辆回到真实道路上行驶,该软件便会悄然关闭这些控制系统,导致实际排放的氮氧化物飙升至法定限值的40倍之多。大众集团最终承认,在全球范围内数百万辆柴油车上安装了这款作弊软件。
这场风暴的中心,站着一个象征着旧时代权威的人物——马丁·文德恩。作为大众汽车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他被视为德国工程师文化的化身:严谨、强势、对细节有着近乎痴迷的控制力。在他的领导下,大众汽车一路高歌猛进,在2015年上半年一度超越丰田,登顶全球销量冠军的宝座。
然而,正是这位看似无所不能的汽车沙皇,却有着一个致命的战略盲点。他曾频繁地公开表示,插电式混合动力才是未来,并断言纯电动车的续航里程不会超过150公里。在这种判断下,大众将大部分资源都倾注于所谓的“清洁柴油”技术。
丑闻曝光后的第五天,文德恩被迫宣布辞职。他发表了一份声明,这段话将作为企业危机公关史上的经典案例被反复研究。他说道:“我这样做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尽管我个人并未意识到任何不当行为。”一位以掌控细节闻名的CEO,声称对自己公司内发生的长达数年、涉及数百万辆汽车的系统性欺诈毫不知情。
就在德国汽车工业的巨人们因自身的傲慢与欺骗而踉跄倒地之时,一场截然不同的革命正在中国悄然酝愈。一群大多来自互联网和科技领域的创业者,正以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闯入这个百年行业。他们不迷恋发动机的轰鸣,也不执着于纽博格林的圈速。他们是产品经理、用户体验设计师和AI梦想家。
这群新物种带来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资本,而是一种全新的造车哲学。蔚来的李斌将汽车重新定义为一种持续的“服务”,致力于打造一个“用户企业”;理想的李想则将其定义为一个“移动的家”,将焦点从驾驶者转向了整个家庭的乘坐体验;而小鹏的何小鹏,则将赌注全部押在了软件和AI上,试图将汽车打造成一个“带轮子的智能设备”。他们没有试图在德国人最擅长的领域与之正面竞争,而是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
除了这几位声势浩大的互联网“闯入者”,还有一位沉默的“局内人”——比亚迪的王传福。与新势力们高举高打的发布会和天马行空的用户故事不同,王传福和他执掌的比亚迪,走的是一条截然相反、甚至有些“土气”的道路。他是一位工程师,不是产品经理,他信奉的是技术自研和垂直整合,而非轻资产和用户运营。
在2015到2020年这段时间里,当新势力们凭借炫酷的设计、流畅的车机和新颖的服务模式吸引眼球时,比亚迪常常因其“老气”的设计和乏善可陈的智能化体验而受到嘲讽。在资本市场眼中,它的故事远不如蔚来们性感。
但外界的喧嚣并未动摇王传福的战略。他像一个固执的农夫,低着头默默耕耘自己那片不被看好的土地:电池、电机、电控,甚至车规级芯片。他痴迷于掌握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从上游的锂矿,到下游的整车制造,试图将所有核心技术都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这种“什么都自己干”的重资产模式,在当时看来笨重且低效,却在不经意间为比亚迪构筑了一道深不可测的护城河。当其他车企——包括新势力和传统巨头——都依赖外部供应商提供“三电”系统和智能化解决方案时,比亚迪却拥有了定义和控制核心零部件成本与性能的绝对能力。
决定性的分野,最终并非源于政策的差异,而是产业基因的突变。中国的挑战者们,无论是来自互联网的新贵,还是来自制造业的老兵,都用自己的方式,从不同维度对传统汽车发起了攻击。当竞争的赛道从发动机和变速箱转向操作系统、三电技术和用户体验时,德国的工业巨匠们发现,他们正在用旧地图打一场新战争。
当哲学上的分歧演变为市场上可见的差距时,一个曾经被认为绝无可能的时刻到来了。在沃尔夫斯堡的玻璃大厦内,一个名为CARIAD的数字幽灵,一直困扰着整个大众帝国。这个被寄予厚望、旨在为集团旗下所有品牌开发统一操作系统的软件部门,变成了一个耗资数十亿欧元的巨大瓶颈。
CARIAD的开发过程充满了内部政治斗争、技术路线的混乱和文化的冲突。来自奥迪、保时捷和大众不同部门的工程师们,带着各自的骄傲和工作方式,难以有效协同。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德国汽车工业那种为完美硬件而生的、严谨的、长周期的瀑布式开发流程,与软件世界所要求的敏捷、迭代、快速试错的文化格格不入。一位身处其中的工程师曾抱怨德国企业文化“官僚得令人痛苦”,充满了无休止的会议和责任推诿。
这场文化冲突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软件平台的开发一再延迟,漏洞百出,直接导致了大众集团多款关键电动车型的上市时间被推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基于全新PPE高端电动平台的保时捷Macan EV和奥迪Q6 e-tron,这两款被视为对抗特斯拉和中国高端电动SUV的战略车型,其发布时间被迫推迟了一年多。这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更严重损害了大众在电动化转型中的声誉和市场先机。
在残酷的市场现实面前,大众汽车集团开始艰难地调整姿态。过去,大众在中国的战略是全球战略的延伸,将在德国开发的平台和技术引入中国。但随着ID.系列电动车在中国市场的表现远未达到预期,这种“老师教学生”的模式失灵了。于是,“在中国,为中国”的战略应运而生。这句口号背后,是一种深刻的战略转变,是从全球统一平台到承认中国市场特殊性、并进行本土化深度研发的巨大让步。
2023年7月,大众宣布向成立不到十年的小鹏汽车投资约7亿美元,收购其4.99%的股份。这笔交易的实质远非财务投资那么简单。协议的核心内容是技术合作:双方将共同为大众汽车品牌开发两款专为中国市场设计的B级电动车型。更深层次的合作在于底层技术,大众将采用小鹏的电子电气架构——这相当于汽车的“中枢神经系统”和“大脑”。
这个决策的意义是颠覆性的。就在几年前,大众还试图通过自家的CARIAD来掌控软件和电子架构的未来。而现在,这家因软件作弊而陷入危机的公司,正在向一家中国初创企业购买其最核心的软件和电子技术——这无异于一场“技术输血”。大众集团负责中国区业务的管理董事贝瑞德明确指出,通过与小鹏的合作,大众将“缩短产品开发周期,提高效率,并优化成本结构”。
几乎在同一时间,大众旗下的豪华品牌奥迪宣布,将与其中方合作伙伴上汽集团深化合作,共同开发一个全新的高端智能网联电动车平台。奥迪首席执行官高德诺的表述更为直接,他称合作的目标是,结合“奥迪的豪华体验和上汽在中国的创新速度”。
德方高管口中的“中国速度”,很快从一个感性概念,被权威咨询机构量化为行业基准。麦肯锡公司的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已将一款全新车型从概念设计到上市的开发周期,缩短至约24个月。
相比之下,传统的西方汽车制造商通常需要40至50个月。这种惊人的速度并非仅仅依靠加班,而是一套系统性优势的体现:软硬件开发解耦,高达65%的测试工作通过软件模拟和虚拟原型完成,以及位于长三角地区的整车厂可以在短短4小时内获得所有需要的零部件。
从1980年代大众在中国投资建厂,手把手教中国工人如何组装一台桑塔纳开始,中德汽车的合作关系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始终是“老师”与“学生”的模式。而大众与小鹏的联姻,则为这个长达四十年的故事画上了一个戏剧性的句号。当德国的硬件资本,不得不向中国的软件专业知识低头时,传统的师徒关系开始瓦解。
这场发端于中国本土的变革,其影响早已溢出边界,直接冲击着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的工业心脏。过去被视为遥远学徒的中国汽车工业,如今已经兵临城下。
在曾经由三叉星徽和蓝白螺旋桨统治的德国高速公路上,新的字符开始出现。德国联邦机动车运输管理局(KBA)的官方数据,记录下了一些看起来更像是笔误而非销售数据的增长率:2024年上半年,比亚迪在德国的新车注册量同比增长了427.2%,长城汽车则同比增长了118.9%。
更重要的是,新一代的中国汽车正在赢得欧洲最严苛、最权威机构的认可。2023年,小鹏汽车的旗舰SUV G9和轿车P7,相继获得了欧洲新车安全评鉴协会(Euro NCAP)的五星安全评级,有力地回击了外界对中国汽车安全性的传统偏见。蔚来的旗舰轿车ET7,在刚刚登陆欧洲市场仅几周后,便击败了众多本土竞争对手,赢得了被誉为“德国汽车界奥斯卡”的“金方向盘奖”。
这场逆转的本质,不仅仅是工业实力的此消彼长,更是文化和技术范式的根本性变革。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好车”的定义由德国人书写,它关乎机械的精度、发动机的功率和底盘的极限。而现在,这个定义正在被重新书写。一辆“好车”的核心,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其软件的智能程度、座舱的体验愉悦度以及生态服务的完善度。
一个世纪以来由内燃机和机械工程主导的时代已经落幕,一个由代码、数据和用户体验定义的新时代已经到来。而这场中德之间戏剧性的角色互换,仅仅是这个新时代序曲的第一章。
2024年9月,大众做出了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决定:单方面终止已持续三十多年的就业保障协议,在德国境内关闭至少三家工厂,裁员近万人,同时还计划全员降薪 10%。这在大众80多年历史上属于首次,也是在过去多轮经济危机中都没有发生过的变故。
德国工会组织极其强大,甚至能够影响企业决策,大众汽车公司的监事会席位中,就有半数来自工会成员,对公司的重大决策有着很大影响力。这次大众宣布关厂裁员,工会立刻站出来抗议,表示“将坚决抵抗这场对我们工作岗位发动的历史性攻击”。
只不过,再怎么抗议也抵不过形势逼人。这次大众陷入漩涡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市场占据着大众40%的业务份额,而大众的电动车项目没能搭上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东风,在这个最重要的海外市场正快速失血掉队。对于大众这次史无前例的危机,媒体的评价是“成也中国,败也中国。”
2019年是大众汽车的巅峰,无论全球还是中国销量均为历年最高。但经历了随后 4 年的行业变化,全球销量下滑了 170 万辆,在中国销量就掉了 100 万辆,被丰田拉开了 200 万辆的差距。 大众丢掉的市场份额,基本都被崛起的国产厂商承接,尤其是比亚迪,如今已超越大众成了中国汽车市场的老大。
随着规模下滑,大众在全球市场的定价话语权将被逐步削弱,很难维持与丰田等巨头之间现有的竞争局面。
这一幕在另一个领域似曾相识。在手机的功能机时代,国产手机被打的满地找牙毫无存在感,但在苹果掀起的智能机热潮中,国产手机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便攻城略地,不但收复了失地,今日已足以与世界巨头争雄。
当然,汽车制造的复杂性,汽车行业对安全性可靠性的要求,比消费级电子产品高得多。毕竟,iPhone在零下温度自动关机也就在朋友圈让大家乐一下,而汽车在东北零下几十度开着开着自动关机,可就是要人命的事了。
这场跨越四十年的逆转,时至今日其结局早已超越了商业竞争的范畴。这不再仅仅是关于汽车的兴衰,而是关于一个国家工业能力的变迁,更是关于在下一个时代,谁能定义“先进”与“未来”的产业叙事。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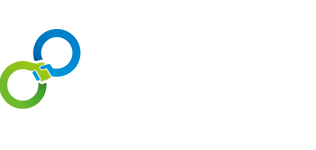
 2025-09-27 12:38:14
2025-09-27 12:38:14 浏览次数: 次
浏览次数: 次 返回列表
返回列表 友情链接:
友情链接:





